追憶盧緒章文/張榮明 中化公司原副總經(jīng)理 |
|
握住先生的手,側(cè)眼瞥見先生手上厚厚的老繭,我的眼眶濕潤(rùn)了 俗話說,少好幻想,老好回憶。耄耋之年回憶起眷眷浮生,諸多人事在腦海中揮之不去。挑燈伏案,追憶與盧緒章同志接觸點(diǎn)滴,傾往昔、訴衷腸。 盧緒章1911年6月出生于浙江省鄞縣一個(gè)商人家庭。用他的話說,“早些年世道動(dòng)蕩,也嘗試過不少事情”。 他曾在輪船公司當(dāng)過伙計(jì),也參加過童子軍。青少年時(shí)期,因目睹社會(huì)黑暗與腐敗,萌發(fā)了對(duì)舊制度的不滿和反帝反封建思想。1936年,25歲的盧緒章請(qǐng)?jiān)竻⒓由虾B殬I(yè)界救國(guó)會(huì)。在救國(guó)會(huì)里,他接觸了馬克思主義,深刻認(rèn)同無產(chǎn)階級(jí)聯(lián)合起來才能改變中國(guó)的命運(yùn)。 1937年,他秘密加入中國(guó)共產(chǎn)黨。1939年,組織決定由盧緒章同志擔(dān)負(fù)為黨的地下組織籌措經(jīng)費(fèi)的任務(wù),擔(dān)任廣大華行總經(jīng)理,利用廣大華行作為黨的地下經(jīng)濟(jì)企業(yè)。他遵照黨的指示,“長(zhǎng)期隱蔽,積蓄力量,等待時(shí)機(jī)”。 盧緒章在領(lǐng)導(dǎo)廣大華行近10年的時(shí)間里,經(jīng)常要與國(guó)民黨高官和大資本家打交道,還要在中統(tǒng)、軍統(tǒng)特務(wù)的眼皮子底下斡旋,可以說是“和魔鬼打交道的人”。在如此艱難的局面下,他依舊取得了突出的工作成績(jī),為解決黨的地下組織經(jīng)費(fèi)問題發(fā)揮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中央高度贊賞。 1950年12月,盧緒章任中國(guó)進(jìn)出口公司總經(jīng)理。也是從那個(gè)時(shí)候起,我有機(jī)會(huì)近距離接觸這位傳奇人物。 1954年,我從外貿(mào)學(xué)院畢業(yè),分配到外貿(mào)部三局工作。盧緒章是三局的主管領(lǐng)導(dǎo),我得以有比較長(zhǎng)的時(shí)間接觸他,得到他的教誨。 那個(gè)年代的人,大體上不講究穿著,用現(xiàn)在的話講,叫不懂時(shí)尚。盧緒章則不同,他身材魁梧,風(fēng)度翩翩,衣著得體,氣宇軒昂,總是流露出一種超凡的氣質(zhì)。 初與盧緒章見面時(shí),他不茍言笑,話語簡(jiǎn)潔,有著濃重的寧波口音,很容易讓后輩產(chǎn)生敬畏感。但相處幾天之后,我改變了對(duì)先生的看法。他對(duì)年輕人非常愛護(hù),從不嚴(yán)厲呵斥,有時(shí)候會(huì)開個(gè)小玩笑來緩和氣氛。 盧緒章十分好客,假日常邀請(qǐng)我們?nèi)ニ抑凶隹停看稳ハ壬遥加X得收獲頗多。一來他愛讀書,也收藏了很多書報(bào)和雜志,許多藏品是市面上買不到的,他允許我們隨便翻閱,也經(jīng)常和我們分享他的閱讀心得,讓我增長(zhǎng)知識(shí)、開闊眼界;二來他愛留客,每次拜訪總是安排嫂子為我們備飯,暢敘時(shí)事之后能夠吃上一碗熱乎乎的菜肉餛飩,是我很期待的事情,我曾私底下把去先生家做客當(dāng)作打牙祭的好機(jī)會(huì)。 盧緒章興趣廣泛,尤其鐘愛橋牌。他常說,橋牌的本質(zhì)是博弈,而生活本身就是一場(chǎng)博弈。同先生一起打過幾次橋牌,我感覺橋牌的樂趣在于少靠運(yùn)氣、多憑智慧。在打牌過程中,要運(yùn)用很多數(shù)學(xué)、邏輯學(xué)的知識(shí),計(jì)算和記憶能力在橋牌中非常重要。有次我與先生打牌,席間問及為何如此鐘愛這項(xiàng)活動(dòng),他笑道:“能打好牌,不一定能做好事,但打不好橋牌,怕是一定做不好事。”只言片語間,不難想象先生為了崇高的革命信仰隱藏身份從事地下工作的壓力與艱辛。
盧緒章立場(chǎng)堅(jiān)定,一生經(jīng)歷風(fēng)雨卻從未動(dòng)搖過自己的信仰。文化大革命期間,先生也受到了迫害。因?yàn)樵L(zhǎng)期在白區(qū)工作,造反派以此為由給他扣上“叛徒特務(wù)”的帽子,專案組派了一批又一批人去調(diào)查他的投敵叛變行為,卻一無所獲。即使如此,先生還是被下放并繼續(xù)接受審查。 一個(gè)初冬的早晨,我與即將去下放的盧緒章匆匆見了一面,他穿著厚重的軍大衣,胡子還沒來得及刮,臉上、眉毛上滿是塵土,著實(shí)憔悴了不少。先生看著我,什么話都沒有說,沖我點(diǎn)點(diǎn)頭,然后揮手致意。令我驚訝的是,先生的眼神中沒有恐懼,也沒有消沉,反而異常堅(jiān)定。 再后來,我與盧緒章在下放的勞動(dòng)場(chǎng)見過一次面,他干活很是賣力,看著他不停地擦汗,我著實(shí)心疼。等到?jīng)]有旁人在場(chǎng)的時(shí)候,我小心翼翼地湊過去問:“您說這文化大革命什么時(shí)候才能結(jié)束呢?”先生拍了拍我的肩膀,語重心長(zhǎng)地說:“小張,你還年輕,一定能看得到,要相信黨。”握住先生的手,側(cè)眼瞥見他手上厚厚的老繭,我的眼眶濕潤(rùn)了。 那一刻,我有點(diǎn)分不清風(fēng)度翩翩與寡言深沉,哪個(gè)才是先生最本真的模樣,但我堅(jiān)信,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外表下,都懷揣著一顆赤誠(chéng)堅(jiān)定的心。 耄耋之年憶往昔,自覺平生多感激。正己立身?yè)P(yáng)正氣,赤誠(chéng)無懼眾心依。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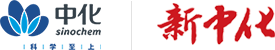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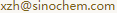



 建議(1024*768) IE7.0以上瀏覽器瀏覽本站
建議(1024*768) IE7.0以上瀏覽器瀏覽本站




